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对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葬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作了初步研究,分别探讨了各个星宿画面的名称及含义,证明这个星图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示意性质的圆式天文星图(“盖图”)。它的发现还把我国绘制全天星图的可靠历史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

▲ 图一 太阳
1987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院内发现一座汉代砖室墓葬。据专家组鉴定,其年代约当西汉晚期宣、元之后、王莽之前(约公元前73-公元8年),距今约二千年。墓葬内最重要的发现是绘满了墓室内壁的彩色壁画。壁画可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中间用朱红色菱形几何纹隔开。壁画下部画的是象征性的波浪状山川及在山中觅食的虎、鹿、野猪、天鹅等禽兽,它们代表人类生活的大地。壁画上半部分,主要是墓室顶部画的是天象图。墓室正顶中线南侧画着一轮朱红色的太阳,太阳中间有一只飞翔的黑色金鸟(图一);中线北侧画着一轮白色的月亮,月中有一只蟾蜍和一只奔跑的兔子(图二)。太阳和月亮四周绘满了彩色祥云,祥云中间还有几只振翅高飞的仙鹤。环亘墓室顶部有一条内径约2.20米-2.28米、外径约2.68米-2.70米的环状圆带将太阳和月亮围在中间。壁画最重要的内容——二十八宿天文星图便画在这个环带当中(图三)。这个星图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现。本文力图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个星图作一些初步的分析考证。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 图二 月亮

▲ 图三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室顶部壁画画面(摹本)
一
关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体系,中外学者已有过不少论证(钱宝琮;竺可桢;夏鼐;J. Needham等)。尽管对二十八宿体系起源及形成的时限说法不一,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它已非常成熟。除了《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之外,年代约当战国初期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土的漆箱盖上已列有完备的二十八宿宿名(王健民等)。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甘、石《星经》已载有二十八宿的坐标位置值。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牍书籍中用于占卜吉凶的《日书》,其中不仅有完备的二十八宿宿名,还提到了招摇、玄戈等星的名字。
汉代是我国天文学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如《淮南子》,《史记》等不仅对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等有详细的观测记录,而且汉代的墓葬壁画、画像石等艺术中也有许多天文星象图。就目前所知,西安交通大学汉代壁画墓中的二十八宿星图(以下简称“西安交大汉墓星图”)是汉代天文星象文物遗存中较为完整的一个,其内容最为丰富。从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幅二十八宿星图是汉代天人之学盛行、神仙思想弥漫的产物。如《史记·天官书》实际是一篇占星术。即使像张衡这样的大科学也认为,“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灵宪》)西安交大汉墓星图便是从属于“升仙”的壁画主题,表达着死者对天上世界的向往。

▲ 图四 亢宿、氐宿、房宿
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绘制天文星图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或更早。《汉书·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说明作者在写作时是有图可资的。西汉初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对彗星的各种形状已有比较精确的描绘(席泽宗)。以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内容较为完备天文星图皆为唐代以后之物。唐代以前的天文星图虽屡见于历史记载,但都已失传。从理论上讲,星图既是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记录,它反过来又可以帮助天文学家通过星图了解天象。所以,只要天文科学达到一定的水平,天文学家对星象的观测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天文星图便有可能产生。冯时先生把1987年6月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虎墓穴确定为中国最原始的盖图的论点颇有道理。他对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漆箱盖和漆箱的东、北、西三面图案的分析也证明,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已出现了表达较为准确的天文星图(冯时;钱宝琮)。这个结论也许并不过分。但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那些星图装饰性太强,使人无法借之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天文星图的绘制情况。相比而言,西安交大汉墓星图要详备得多,表达也更准确、生动。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汉代天文星图实物,更使我们能通过对这幅星图的研究分析,了解到有关汉代天文星图、汉代天文科学水平的更多信息。

▲ 图五 心宿、尾宿
东汉末年,蔡邕在《月令章句》中对当时天文史官所使用的天文星图(“官图”)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天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经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官图内赤小规是也。谓乎恒星图(疑为“圈”之误)也。绕南极经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大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察东西,则天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开元占经》卷一)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幅“官图”是我国传统天文星图中“盖图”即圆式星图的典型范本。以前,这段文字得不到有力的旁证,因为现存的各代星图都远晚于蔡邕的时代。西安交大汉墓星图的发现,不仅可以证明蔡邕这段话的准确可靠,更把我国出现圆型全天星图(盖图)的可靠历史上推到公元前一世纪或更早。

▲ 图六 危宿、虚宿
西安交大汉墓星图正是画在一个巨大的同心圆形环带之内(图三)。二十八个星宿沿环带分布,正好组成一个周天。壁画作者在作画时可能是有所根据的,因为画这样一幅天文星图需要相当的天文科学知识,而这显然非一般的民间画工所能办到。考虑到它从属于“升仙”的壁画主题,在画法上也只能是示意性的。但作者力图向人们表明这二十八个星宿代表全天星宿这一点却不容怀疑。加上太阳和月亮,这种示意性就更生动、完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幅星图视为一幅示意性质的圆形全天星图。
从画面来看,壁画中的二十八宿星图完全是依据中国古代对二十八宿体系的传统划分方法来画的,即将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并和四个地平方位(东、北、西、南)、四种颜色(青、黑、白、红)、四组五种动物形象,即四象(青龙或苍龙、玄武、白虎、朱鸟)相对应。在画法上,东宫青龙在用墨线勾勒出轮廓之后,再用渲染法在龙身上涂上一层淡青色(图四、图五),十分传神。北宫玄武则省略了神龟,而仅用一条黑色的小蛇来代表(图六)。西宫白虎完全画成白色(图七)。唯一不同的是南宫朱鸟并未画成红色,而画成一只淡青色的头向西方的大鸟,其形象极类似于凤(图八)。除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龙虎图像外(冯时),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也画有与二十八宿名称相配的青龙、白虎图象(王健民等)。西安交大汉墓星图中的四象形象则是目前已知的将四象与二十八宿星图相配的最完整的范例。

▲ 图七 参宿
在星图的具体表现方法上,该墓壁画也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是,壁画作者把天文知识和神话传说融合在一起,把各个星宿融合于人物、动物形象之中,画面完整,表达准确;其次,用小圆圈代表恒星,而用直线连接各个小圆圈(恒星)以表示星官是中国古代绘制星图的传统方法之一,汉代画像石上便已有这样的例子(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刻画像星象图)。西安交大汉墓星图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这种绘图法的最早范例。壁画作者在白色的底子上用墨线勾画出一个个直径3-4厘米不等的圆圈来代表各颗恒星;一颗星、或几颗星用直线相连组成一个星群以代表一个或两个星宿。各宿恒星井然有序,使人一目了然。

▲ 图八 大鸟(朱鸟)
二
下面我们从东宫七宿开始,对壁画中的各个星宿逐个加以分析。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东宫七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组合起来,南首北尾,正像一条腾跃的巨龙。不管龙的形象起源于什么,这六个星宿的得名确实都和龙的形体有关(冯时)。其中,角宿象征龙的角。《史记·天官书》:“杓携龙角”,《集解》引孟康曰:“龙角,东方宿也。”一般认为,角宿是两颗星。《史记·天官书》又云:“左角,李;右角,将。”但壁画中的角宿实际画出了四颗星:龙的左右两角顶端各有一颗星,右角中间小叉角的顶端画有一颗星,与之相对的左角中间小叉角端也似有一颗星。这一部分壁画虽然损坏严重,但仍留有明显的连接线痕迹(图三)。笔者认为,壁画中所画的角宿可能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角宿二星(室女座υ、ζ),而可能画的是天门二星(室女座53、69)和天田二星(室女座78、τ)。《史记·天官书》裴骃《集解》引石氏云:“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门”。这种说法远早于《史记》。类似的将角宿刻画为四颗星的例子还有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一幅苍龙星座图。图中所刻角宿恰为四颗星,一边两颗(图九)。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 图九 苍龙星座
角宿往下,龙的四只爪子各抓着一颗星,龙的尾端也有一颗星。这五颗星应分别代表着亢、氐、房、心、尾这五个星宿。
亢宿(四星):《说文》:“亢,人颈也。”亢又作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贯高)乃仰绝肮,遂死。”《集解》引韦昭曰:“肮,咽也。”可见亢宿四星象征龙的咽喉。壁画中的亢宿以龙的右边第一爪抓着的一颗星来代表(图四右,已损)。这颗星应为亢宿的古距星亢宿一(室女座χ)。
氐宿(四星):《史记·天官书》:“氐为天根,主疫”。又《尔雅·释天》云:“天根,氐也。”《日书》又写为“牴”。《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引》引孙炎以为:“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也。”壁画中的氐宿以龙的左边第一爪抓着的一颗星来代表(图四,中)。这颗星应为氐宿距星氐宿一(天秤座α)。
房宿(四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石氏星经》:“东宫苍龙七宿,房为腹。”故房宿象征龙身。《史记·天官书》又云:“房为府,曰天驷”。房宿四星一字排开,像四匹驾车的马,故曰“天驷”。壁画中的房宿(图五,右下),代表星应为房宿距星房宿一(天蝎座π)。
心宿(三星):《史记·天官书》:“心为明堂”。《索隐》引《春秋说题辞》云:“房、心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心宿应象征苍龙之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壁画中的心宿代表星画成一颗朱红色的巨星(图五,左)。这颗星显然是心宿三星的古距星,也是最有名的红色巨星——心宿二,即大火星(天蝎座α)。出于观象授时的需要,心宿二是我国古人认识最早的恒星之一,从原始社会起它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观测。《史记》载帝颛顼命“火正”黎专司观测大火星;《夏小正》有“五月初昏大火中”、“九月内火”;《诗·豳风》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句;《左传》中更有许多关于大火星的记事(《左传》载: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又昭公九年,“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此外,大火星的形象不仅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上,还被特别描绘在曾侯乙墓漆箱盖的东宫向立面上(冯时)。壁画作者特意将其画成红色,显然是为了突出这颗星的特殊地位。
尾宿(九星):《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尾宿九颗星弯成一个弧形,正象征着龙尾。壁画在龙的尾端画出一颗星以代表尾宿九星。从位置来看,这颗星应该是尾宿的古距星尾宿八(天蝎座λ)。尾宿九星中也以这颗星最为明亮(二等星)。在汉代画像石的苍龙星座图中,尾宿被刻画得比较充分。如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两幅苍龙星座图,一幅中的尾宿刻出五颗星(图九),另一幅刻出了七颗星(图一〇)。

▲ 图一〇 月苍龙星座
箕宿(四星):《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舌。”《索隐》引宋均云:“敖,调弄也。箕以簸扬,调弄象也。箕又受物,有去去来来,客之象也。”箕宿之得名,显然是因为箕宿四星连接起来的形状和古代用于扬米去糠的簸箕相像。四星中二星为踵,二星为舌,踵窄舌宽。箕的簸扬功能又引申为多嘴多舌,搬弄是非。《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箕宿又称为“南箕”。《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壁画中的箕宿画成一个身穿襦袍、头上戴冠的男子踞地而坐,双手像是执着箕踵。男子右边是箕宿四星(图三)。
箕宿之后,壁画画着一个身穿长袍的男子分腿站立,身子略向前倾,右手执一星,身子右边有五颗星。六颗星连成斗形,右四星为斗体,左二星为斗柄(图一一)。此即斗宿。斗宿在汉代又称“南斗”。《史记·天官书》:“南斗为庙”。斗宿显然因其六星相连像古代的容量器“斗”而得名,又因其和北斗七星相对而称南斗。又箕、斗二宿古代经常连称。如《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播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 图一一 斗宿
斗宿之后是牛宿(六星)。壁画画着一个回头张望的男子手里牵着一条牛,牛腹之上有一线三颗星(图一二)。牛宿在汉代又叫“牵牛”。六星中除中间一星(摩羯座β)较为明亮(三等星)之外,北面二星(实为四星,其中三颗为双星)和南面三星(皆为双星)都较暗弱,且簇拥在一起。所以壁画只以牛腹上的一线三星来代表。以人牵牛的形象代表牛宿还出现于汉代画像石中,但被误释为牛郎星,即河鼓三星(天鹰座β、α、γ)(吴曾德、周到)。牵牛六星与河鼓三星在古代正史中有明确区分。《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正义》云:“河鼓三星,在牵牛北,......自昔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此星也。”但在先秦时期,民间便将河鼓三星也称为“牵牛”,并引出牛郎织女的传说。《日书》云:“戊申己酉,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尔雅·释天》亦云:“河鼓谓之牵牛”。可见这两个星官之名在民间相混由来已久。但传说中的牛郎星确指河鼓三星而非指牛宿,魏晋以来的文献都对此有明确的区分。《初学记》卷四引晋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从星象上讲,牛宿六星与织女三星(天琴座α、ε、ζ)相距遥远,似难联系在一起。所以,与该墓壁画相似的南阳汉画像石中以人牵牛的形象也应释为牛宿。

▲ 图一二 牛宿
女宿四星,汉代以前又叫婺女,也叫须女。《史记·天官书》:“婺女,其北织女”。《索引》引《广雅》云:“须女谓之婺女”。《正义》云:“须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该墓壁画中的女宿画成一个踞坐袖手的女子形象。女子右边有两颗星,左下方也有一颗星(图一三)。壁画作者把女子的头画成圆形,似乎也指代一颗星,加在一起正是四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星图,在左下角刻着一组不规则的四连星,四颗星中间有一个跪着的女子(吴曾德、周到)。它所刻画的正是女宿的形象,但被误释为织女星。

▲ 图一三 女宿
从北宫玄武七宿中的虚宿往下至西宫白虎七宿中的毕宿,共有虚、危、室、壁、奎、娄、胃、昴八个星宿。而壁画中的这一段星图却只画出了六个星组。所以在这一段星图中应有两个星宿被与别的星宿合画在一起。或者说,在汉代它们或是名称有别而实际作为一个星宿,或是连称而被合在一起。另外,这一段星图中的个别星宿,如娄,昴等宿损坏严重,无法看清详细的绘制情况,故只能结合文献作一些初步的推断。
壁画中在女宿之后,画着连成横放的宝塔形的一组五颗星,五颗星中间有一条黑色的蛇(图六中)。这一组星所代表的,应该是虚宿和危宿。《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古代虚同墟,可引申为旧宅荒废,居宅无人,故主“哭泣之事”。虚宿二星都是比较暗弱的三、四等星,且相距较远,显得很空阔,正似“虚”之空旷。又虚、危二宿正当十二次中的玄枵。《尔雅·释天》:“玄枵、虚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云:“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故《史记·天官书》《正义》云:“虚二星、危三星,为玄枵”;“虚主死丧哭泣之事,......危为宗庙祀事,主天市驾屋”。《索隐》引宋均云:“危上一星高,旁两星随下,似乎盖屋也。”危宿三星一星高二星低,形似屋脊,故曰“危”。壁画中这一组五颗星的左边三颗星正是一星在顶,两星两旁随下,形似金字塔顶。此外,虚、危二宿古代合称“北陆”。《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尔雅·释天》:“北陆,虚也”。《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孙炎曰:“陆,中也,北方之宿中也。”壁画中这一组五颗星的位置基本处在墓顶南北中线的北端,代表北宫七宿的玄武形象也画在这里,只是略去了灵龟而只画出一条小蛇。这可能是因为地方太小。所以,根据虚、危二宿在古代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组五颗星中的右边两颗星是代表虚宿二星(小马座α、宝瓶座β),左边三颗星则代表着危宿三星(宝瓶座α、飞马座θ、ε)。
虚、危之后,是室宿和壁宿。在汉代以前,室、壁二宿时分时合,有时分称为营室、东壁,有时合称为定,或叫营室。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春秋以前,这两个星宿是合为一个星宿的,以后才逐渐分开(竺可祯;夏鼐)。《诗·鄘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毛《传》云:“定,营室也;方中,昏正四方”;郑《笺》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定昏中而正,谓小雪时,其体与东壁连正四方”。《尔雅·释天》:“营室谓之定”。郭璞注云:“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中为正”。《开元占经》卷六一引郗萌云:“营室二星为西壁,与东壁二星合而为四,其形开方似口。”室宿二星(飞马座α、β)和壁宿二星(飞马座γ、仙女座α)正像一座房子的东西两壁,故壁宿又称为东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所写的二十八宿宿名将这两个星宿分称为“西萦”和“东萦”(王健民等)。《日书》分称为营室和东壁。《史记·天官书》则只列营室:“营室为清庙”;“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成书于汉代的《春秋元命苞》云“营室十星”,则显然是将室宿带离宫六星(飞马座λ、μ、ο、η、τ、ι)在内的八颗星与东壁二星合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壁画中继虚、危二宿之后的一组四颗星(图一四右)中,右边二星为室宿二星,左边二星为壁宿二星。四星相连,“其形开方似口”,与实际星象基本相符。

▲ 图一四 室宿、壁宿、奎宿
室、壁二宿之后,壁画画着又一组五颗星(图一四中),它们应代表着奎宿十六星。《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读”。《正义》云:“奎,天之府库,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按《说文》:“奎,两髀之间,从大圭声”。段注:“两髀之间,人身宽阔处,故从大。”奎宿的十六颗星连接起来,很像人的盆骨之形,故得名为奎。奎宿是二十八宿中星数最多的星宿之一,不可能全部画出。而壁画中这一组五颗星的连接形状正和奎宿南北两头各星的宝塔形相似。
奎宿之后,画的是一个奔跑的动物形象,动物的身下有两颗星,右上方有一颗星(图一五)。因壁画损坏严重,无法确定画的是什么动物。这一组星和动物所代表的应是娄宿三星。《史记·天官书》:“娄为聚众”。《正义》:“娄三星为苑,牧养牺牲以供祭祀,亦曰聚众”。据此,则壁画中的动物应象征“苑”中所牧养的供祭祀用的动物。而画面中三颗星的各自位置和实际星象中的娄宿三星也十分相象,即动物身下的两颗星应为娄宿一和娄宿二(白羊座β、γ),右上角的那颗星应为娄宿三(白羊座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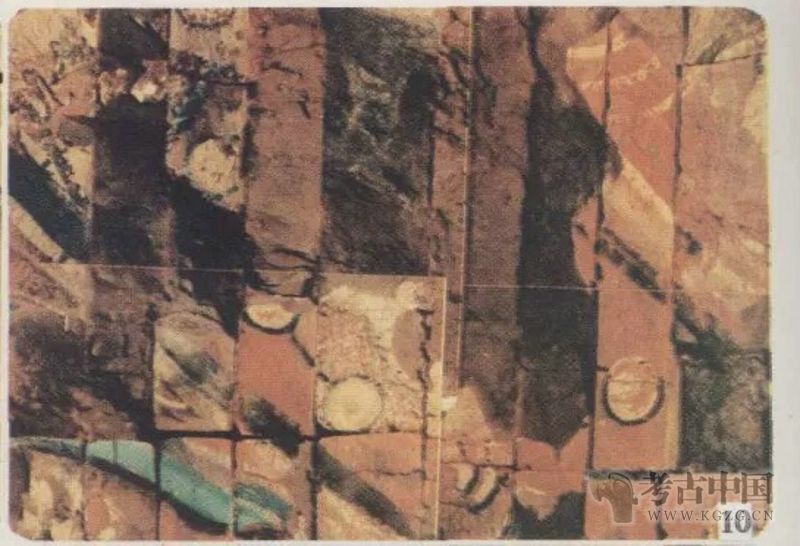
▲ 图一五 娄宿
娄宿之后,当为胃宿(三星)。但壁画中的娄宿之后画的是一组连成环状的六颗星,六颗星中间有一只奔跑的动物。从画面残留的腿、蹄和鬃来看,画的似是一匹马(图一六)。这一组画面实际上应为昴宿,而不可能是胃宿或其它星宿。

▲ 图一六 昴宿
昴宿,即著名的昴星团(金牛座17、19、21、20、23、η、27)。《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按《说文》:“昴,白虎星宿,从日卯声”。《说文》凡从“卯”声者,如留、罶之类,皆含簇拥、团聚之意。《日书》又写作“卯”。而“髦头”正状其攒聚之形。“胡星也”似另有含义。张守节《正义》云:“昴七星为髦头,胡星,……动摇若跳跃者,胡兵大起”。壁画画出胡人所惯骑的马,似即为此。
昴宿之后,毕宿之前的一段壁画画面虽严重损坏,但尚残留有两颗星的痕迹(图一七右)。它有两种可能:一是壁画作者将顺序颠倒而把胃宿三星画在了昴宿之后;另一种则是作者在前面未画胃宿的情况下,在这里补上了其它星官。具体如何还有待研究。

▲ 图一七 毕宿
这之后是毕宿八星。
毕宿之取名,以毕宿八星连接起来的形象象“毕"(古代人掩捕鸟兽用的长柄小网)。《诗·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即说用毕来捕鸟。《日书》云:“毕,以猎、置网及为门吉。”《史记·天官书》《正义》引毛苌云:“毕所以掩兔也”。壁画中的毕宿正画作一只兔子在前面奔逃,后有一人在追赶。此人跨步前倾,双手执着“毕”柄向兔子套过去(图一七)。“毕”由六颗星组成:右边五颗星连成网状,捕兔人身后有一颗星与前面五颗星相连为“毕”柄。奔逃的兔子和追赶的人都画得呼之欲出,十分生动。
毕宿之后是觜宿三星。《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小三星隅置,日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按《说文》:“觜,鸱旧头上角觜也。一曰,觜雟也。”段注:“凡羽族之咮锐,故鸟咮曰觜。俗语因之,凡口皆曰觜,其实本鸟毛角之称也。”壁画中的觜宿画成一只鸱鸮,头上的毛直竖起来似长角一般(图一八)。鸱鸮爪下踩着的两颗星应为觜宿一、觜宿二(猎户座α、ψ1);鸱鸮背后的那颗星应为觜宿三(猎户座ψ2)。鸱鸮头部画面虽已损坏,但仍十分传神。

▲ 图一八 觜宿
参宿七星,约当西方的猎户星座。参本有“三”的含义。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这三颗星是和心宿三星遥遥相对的授时星,所以它们也是中国古人最早认识的恒星。《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而称参宿四至参宿七(猎户座α、γ、χ、β)这四颗星为“左右肩股”。《集解》引孟康云:“参三星者,白虎宿中,东西直,似称衡”。参三星和左右肩股四星都是二等以上的亮星,在黄河流域冬夜的天空中非常明亮,所以古人也容易将这七颗星联系在一起。到《晋书·天文志》便称“参十星”,这显然是将“伐”三星也包括在内。参宿作为西宫七宿的代表星座,在壁画中被画成一只奔跃的猛虎。猛虎的前爪下有一颗星,头顶右上方有一颗星,这两颗星应为“左右肩股”中的两颗;在虎后背和尾巴上方可见残存的连成一线的两颗星。按合理的推测,壁画损坏的部分中还应有一颗星与之相连,这三颗星应即参三星(猎户座ζ、ε、δ)。汉代画像石中也有一些白虎星宿图,一般也把参三星刻在虎背上方(吴曾德、周到)。综起来看,壁画中的参宿所画星数应在五颗以上(图七)。
同样,出于观象授时的需要,南宫七宿中的一些主要星宿也很早便被我们的祖先所认识。在古代的农业生产上,南宫七宿对于标志黄河流域春耕生产季节的到来具有特殊意义。二十八宿的排列顺序便是以我国古代黄河流域春分前后的天象为依据而划定的。此时,正是南宫七宿高悬在南方的天空。
井宿八星,汉以前又称“东井”。《史记·天官书》:“东井为水事”。《索隐》引《春秋元命苞》云:“东井八星,主水衡也”。井宿八星相连适如“井”字。壁画中的井宿省去了四颗星,而画为连成正方形的一组四颗星(图三)。
鬼宿:汉代又称为“舆鬼”。《史记·天官书》:“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质又称为“积尸”或“积尸气”,实为星团。《宋书·天文志》:“积尸气在鬼宿中孛孛然”。《步天歌》云:“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舆鬼之“舆”应为使动用法。壁画中的鬼宿画成一前一后两个人用“舆”(竹篼或担架)抬着一个头上长角、身上有斑点花纹的淡青色怪物(“鬼”),形象非常生动(图一九)。

▲ 图一九 鬼宿(舆鬼)
柳宿和星(七星)、张、翼这四个星宿被古人想象成一只大鸟。其中,柳八星为鸟“注”,“咮”或“喙”;星宿七星为鸟颈;张宿六星为鸟“嗉”;翼宿二十二星为鸟张开的翅膀。《史记·天官书》:“柳为鸟注,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张,嗉,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壁画将这几个星宿合在一起,画成一只淡青色的头向西方的大鸟(图八)。鸟头的右边有上下连成一线的两颗星;鸟身上方(左侧)似有三颗星;鸟下方(右侧)也有三颗星。由于这一段画面代表了柳、星、张、翼四个星宿,我们今天已无法判定具体哪颗星代表哪个星宿。从整个画面来看,壁画作者从角宿画起时,并未按需要将二十八个星宿作均匀分布,而是边画边调整。前面各宿所占画面较大,至参宿已偏到了西南。至柳宿时,所余空间已极其有限,故不得不从简,而将柳、星、张、翼各宿合为一个画面。而从理论上讲,这四个星宿也正合为一只大鸟。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其作严格区分。
二十八宿的最后一宿得名于车轸。《史记·天官书》:“轸为车,主风”。《索隐》引宋均云:“轸四星居中,又有两星为左右辖,车之象也”。壁画中的轸宿四星和实际轸宿四星的星象较为符合(图三)。
三
西安交大附小汉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的绘制情况如上所述。作为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它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总起来看,它与我国古代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吻合,可以互相印证。如壁画中虚宿和危宿的合并、室宿和壁宿的合并都为我国古代史籍中有关这几个星宿的分合演变的记载提供了旁证。再如壁画中女宿和昴宿的画法也使我们得以对汉代画像石及汉代其它艺术中出现的一些星象图作出较为完满的解释。但最后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幅星图是出自当时的民间画工之手,是一种装饰品,是墓葬装饰壁画的一部分,固而它是一幅示意性质的星图,不可能对各个星宿作十分精确的表达。星图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略画、不同星宿之间的不必要连接(如角、轸;毕、觜、参)等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如此,这幅星图仍然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唐代以前的古星图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幅,不失为我国古代天文星图中的一个代表作。它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在汉代取得辉煌成就的真实反映。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